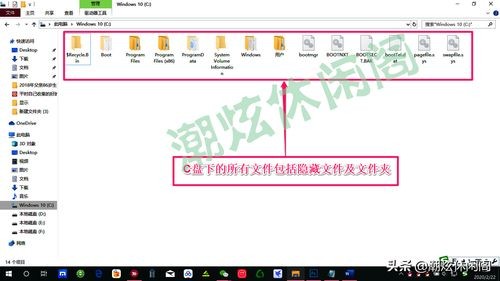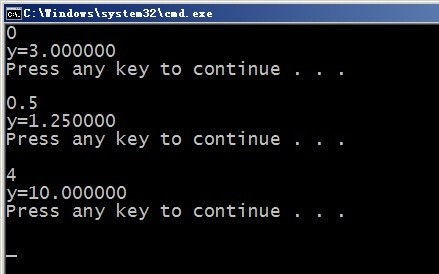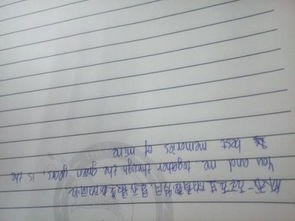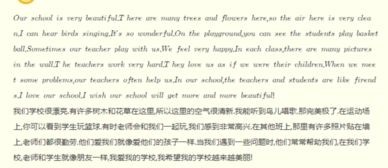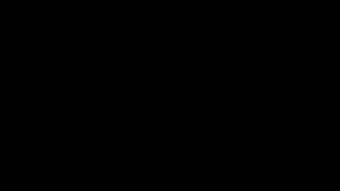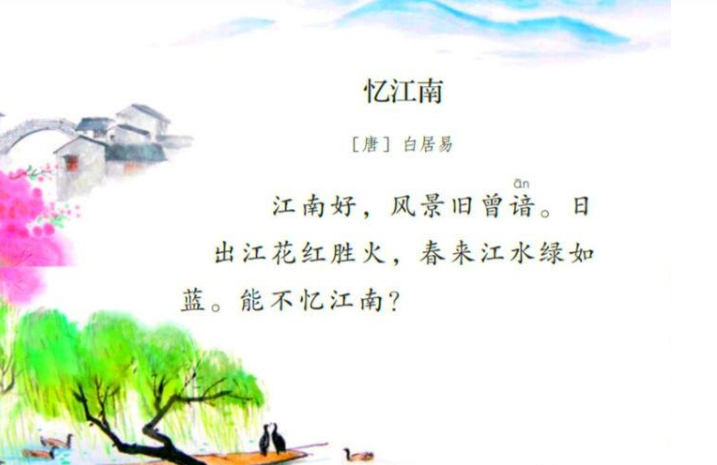elite翻译。周琳

2020年8月20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琳副教授在清华大学明斋337进行了一场题为“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市场、商人和商业制度”的讲座(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对以博士学位论文《传统商业制度及其近代变迁:以清代中后期的重庆为中心》为基础的,为期十二年的研究进行了一个回顾,特别对其中关键问题做了解读。讲座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龙登高教授主持。本文系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内容有删节,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十二年前,这项研究就是从清华园开始的,是李(伯重)老师、龙(登高)老师、仲(伟民)老师、陈(争平)老师指导我一步一步往前走,看着它一点一点“长”起来。今天我终于带着它们齐齐整整地回来了。2010年6月博士论文答辩,是我第一次全面地做这个主题的报告。但其实当时有好多问题都想不清楚、说不清楚。我一直在想,等这项研究做得差不多了,我一定要带着它回母校来再做一次报告。
2010年6月,作者博士论文答辩
十二年了,我一直趴在这些案例、事实和具体的研究题目里,让我从总体上讲一下这项研究,我竟然觉得一时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记得在我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时候,龙老师好几次提醒我,不要被淹没在史料里面。但是现在真的感觉到,要从史料和事实里面跳出来审视一下自己,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把这三十多万字里面的要点盘点出来,再有条理地讲给大家听,真的是有点挑战的。
今天的报告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关于清代重庆市场、社会和人的故事。
相信我,这些故事都是非常扣人心弦的,甚至有时候会让你觉得:这难道是在演电视剧?有好多出人意料的情节。我之所以十二年都蹲在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太有故事了。十二年了,它从来没有停止给我带来惊喜。我写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还是不那么正经的非虚构故事,本质上都像一个站在沙滩上的孩子,不断欢呼着告诉大家:你看这里有一个美丽的贝壳,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如果把这些个案写成一个个的非虚构故事,我敢向大家保证,肯定比现在这本学术书要好看得多。
第二、如何跳出故事,去面对问题。
读博士的时候,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历史学善于发现故事、讲故事,社会科学善于构建理论模理,提供思维工具、构想技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应该互相理解、借鉴对方所长,甚至利用自己的洞见去修正对方的错漏和短板。而不是强行搞同质化,“回敬对方同样一碗粥”(经济学家Robert Solow语,李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引用)。那个时候我是不太懂这句话的,自己的一碗粥都没弄好,哪有功夫去“回敬别人一碗粥”呢?
但是这十年来,这句话会时常地从我的脑海中跳出来,我也越来越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换句话说,社会科学就好像是一套更具有共享性的语言,历史学发现的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故事,一理被“翻译”成这套语言,就可以被放在同一个话语平台、问题框架中去讨论和解释。比如清代重庆城某一条街巷内脚夫们在打架,这看起来是太鸡毛蒜皮、太地方、太草根不过的事情,但是如果把它放到暴力社会学的层面,放到社会治理的层面,甚至放到产权的层面,你就不会觉得发生在三百多年前重庆街头的暴力事件,真的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从暴力这个层面,清代的重庆可以和同一时期的湖北、广东、江西的很多地方放在一起讨论,甚至可以和今天的西西里、圣保罗、芝加哥、香港进行对比。而且恰恰是在这种“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以前认为像数学公式一样的理论或者结论,其实是有改写的空间的,有些甚至根本就是错误的。比如重农抑商、比如封建专制,比如无讼、厌讼、比如女性弱势好欺负,比如传统经济停滞落后、比如中国古代城市的政治职能压倒经济职能等等。
所以,我们在讲了故事以后,一定要让这个故事带出一些大家可以共鸣的东西来,甚至要让这个故事去在一定程度上攻破旧的话语体系,成为新的话语体系构建的起点。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故事要mean something。我从来不相信什么“为了研究而研究”,也不认为一个区域史的研究只是为了发掘“这个地方历史的荣光”,只给本地的父老乡亲们看。我希望也是在努力地让读过我的研究的人们,都能够看到超越这个地区之外的东西,都能够有一种思维层面上的乐趣和获得感。这是我认为整个研究中最难,但又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第三、档案研究的心得。
在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做清代社会经济史的学者,还比较少用档案做为核心史料。以至于我2008年第一次去四川省档案馆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不管是四川本地的学者,还是大老远从外地来的学者,大家都是在看民国档案,没有人看清代的《巴县档案》。当然,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南部档案》《巴县档案》《龙泉档案》《冕宁档案》这些大部头的清代档案汇编一部一部地公开出版。以至于在档案馆你早晨去晚了,大概率连个胶片机都占不着。
所以,如果今天你再说研究《巴县档案》《南部档案》《龙泉档案》,没有人会说你看那玩意儿干啥。但是清代档案它的长处究竟在哪里,与其它的像方志、笔记、调查报告、田野资料相比,它究竟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不一样的信息?另外,要怎样把它比较恰当地用到研究当中去?要怎样避开它里面的那些坑?要怎样做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我想这是只有长期在档案堆里面摸爬滚打的人才能够有所体会的。
我今天在这里这样讲——可能很多同行会不喜欢,但这是一事实,就像档案本身存在虚构一样——利用档案的历史研究其实也容易注水。就说清代的州县档案吧。如果你有机会亲自去摸一下,一定会发现,那里面的东西太多了。只要你把里面的情节巧妙剪辑拼接,想论证什么观点几乎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研究地方档案的同仁们,最大的问题似乎不是找不到材料,而是如何谨慎地约束自己,诚实地面对材料。
第四、我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研究的生命史。
今天在现场和在线上的很多听众都是博士、硕士,所以我特别想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谈一谈这个问题。过去十年我也辅导了很多学生的论文。被问到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老师你看我能写个什么题目?”或者“老师,这个题目写完了我能证明些什么?”这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而应该问你自己,更应该问你的史料:它们想让你写什么?它们想让你怎么写?为什么?因为你才是和它们联结最深的那个人,也是对它责任最大的那个人。这注定是你自己的一个commitment一样的东西,就是一种承诺。
有一本很著名的小说叫做《弗兰肯斯坦》,作者玛丽·雪莱是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这个小说讲有一个叫弗兰肯斯坦的人,他用偷来的尸体制作了一个人。但是在快要完工的时候,他自己被吓跑了,所以这个新的生命就成了一个怪人。这个怪人到哪里都被人嫌弃,不能堂堂正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后来这个怪人就开始复仇,把弗兰肯斯坦原本还不错的小日子完全给毁了。当然,玛丽·雪莱写这部小说,其实是为了反思科学和人的关系。但我仔细想想之后就乐了——这不就是你的博士论文和你的关系吗?你对它呕心沥血,肝脑涂地,它不见得会对你好一点。但是你要是不负责任、做到一半就想跑路,甚至做成一个奇怪的东西,它自然会想各种办法来折磨你。
换句话说,我们做历史研究,从某种角度来看并不是你在创造什么,你常常就像是一个工具或者说一个通道,你的任务是把这些史料想要告诉给这个世界的话传递出来。然后把你自己学术、生活、人生阅历中各种各样的东西注入进去,赋予它一个体面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过去十年几乎没有讲过这项研究,其实就是潜意识里怕自己没有准备好,会扭曲甚至窒息了它。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历史研究一旦开始了,你会看到一些东西在材料的牵引和你的探索之中不断地长出来。它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子,你不会知道。这就是它自己的生命史。与你无关,又与你息息相关。相信这一点,大家在学术这条路上走得越远,就会体会得越深刻。
下面,我们进入三百年前的重庆城,看看这个市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看看那个时候的重庆人是怎样面对他们的生活?
关于“官牙制”
本来,我以为打开《巴县档案》的商业案卷,看到的会是商号、钱庄、票号、店铺、小摊贩什么的,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看到最多的居然是牙行。尤其是1891年重庆开埠之前,关于重庆商业的案子,有一多半都是涉及到牙行的——你看,是不是研究其实是资料“施舍”给你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牙行呢?这是当时重庆市场的一个特殊现象,牵涉到明末清初四川的那一段众所周知的黑暗历史。清代初年的四川就是一个废墟上重生的地区,做生意的人几乎是没有什么土著。比如我是一个从湖北运东西来重庆卖的人,我的船到了码头,我不知道要把这些东西卖给城里的谁;而城里从事批发零售的商家,有很多也是从外地初来乍到的,好多人也没想在这里长待,有些人就是想干一票就走的,有时一个店铺一年就换好几个经营者。所以,买东西的人和卖东西的人都不知道从哪儿去找靠谱的下家,这个时候怎么办?只好求助于中介——就是牙行和牙人了。就像我们今天找房屋中介一样,他可以弥补你信息的缺失。
那如果我在这儿做生意做熟了,是不是就不需要找牙行和牙人了?那也不行。因为《大清律例》有明确规定,所有异地贩售商品的,都要到当地的牙行去登记,给牙行交手续费,让牙行帮你找下家,自己偷偷摸摸地卖掉那是犯法的。这一点是《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的。
《大清律例》中相关律文及例文
一条律文用五条例文来进行补充和说明,这在《大清律例》中并不是很常见的情况。这就说明,国家对这条规定相当重视,国家就是希望让牙行来充当一个监控市场的工具。所以至少在长距离贸易方面,所谓的“自由市场”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不要认为中唐的坊市制解体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越来越自由的市场,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我想找谁买就找谁买。至少在长距离大宗贸易当中,所谓的“自由市场”是理论上不存在的。
理论上不存在,现实上存不存在呢?偷偷摸摸地绕开牙行,私下里交易,牙行还真管得了吗?在清代大部分时候的重庆,还真绕不开,牙行简直是神通广大,一些牙行的眼线遍布全城,就是追到犄角旮旯,也要把那些偷偷进行私下交易的人给揪出来。那么,牙行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都成了这个市场上一个“卡脖子”的存在。明明人家生意做得好好的,他非要到中间来插一杠子,拿一笔中介费走,而且大部分时候还要打着帮助你的旗号坑骗你。这当然不合理,但是如果你去告那些刁难你、敲诈你的牙行,大部分时候是告不赢的。以前有一句俗话叫“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其中就包含着对这种情况的极大不满。
那么,官府明明知道这样对市场没有好处,为什么还袒护这些可恶的家伙?最关键的秘密就在于,这些被称为“官牙”的牙行是要给官府好处的。官府需要人帮着干活了,牙行来办;官府缺乏运营经费了,牙行来解决;甚至官府需要查商人户口了,也是牙行来跑腿。所以官府很多时候对他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讲到这里,你是不是对牙行又有点同情了,原来说“无罪也该杀”,那是只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呀。可是,还是有好多人还挤破头去当牙人呢。清代乾嘉道时期的重庆,获得一个牙行的牌照要向县衙交上千两银子,咸丰年间征收厘金之后,牙行还要帮官府征厘,征不够的还要牙行自己出钱来垫,就这样,还是有很多人争先恐后地要去当牙人。
而且更奇怪的是,牙人向官府提供的差务、报效越多,牙行的发展反而越好。咸丰同治时期重庆牙行征厘压力最大的时候,反而是这整个行业经营最稳定、资本最雄厚、业务最规范的时候。后来官府不用牙行征厘了,整个重庆的牙业反倒很快就走上了末路。
从牙行、牙人的个案当中我开始怀疑两点:
第一就是自由市场。我学习经济史的启蒙书之一,就是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这本书里面所描绘的中国市场,就是一个相当自由顺畅的市场。商品在不同的市场层级之间像水一样川流不息、有条不紊。而且2000年前后关于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论著,大多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描述这个市场的体量、效率、流通能力,总体来说,和施坚雅提供的那个景象非常相似。这也很顺理成章,因为当我们重新开始评价和观察传统市场的时候,总是会从宏观和大处着眼。但是就好像你坐在飞机上,永远看不清底下的城市里哪一条道路在堵车一样。看了极其微观的个案之后,我觉得我并不怀疑老师辈告诉我的那些知识,清代的国内市场的确是有一个质的蜕变。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得有自己的知识增量。那就是传统时代的中国市场可能远不是那么平滑流畅,商品的流动要闯过很多人为的“卡脖子点”,可能要付出比较多的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向人们呈现了一个正交易成本的世界,的确,当你一关心制度,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真不是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虽然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别的地方官府也缺钱,也需要派差,这是事实。所以我怀疑别的地方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别的地方没有这么细致入微的档案。
我怀疑的第二点是“剥削”。我们直觉上认为,官府向商人伸手要钱要东西,肯定是不好事。但是清代重庆的牙人,还有很多的商人群体却未必这么看。有时候他们还主动送上门去让官府来剥削。只要你剥削得不太严重,拿了我的钱和东西帮我办事就好。 反而是官府不剥削商人了,商业就危险了。 这一点在我的研究中反复地得到证明。所以,历史学研究可能有时候还需要一点“当事人视角”,才能更加全面地呈现一个事情在人们眼中的样子。
八省客长
最早,我是从罗威廉关于汉口的两本书里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在这两本书里面,罗威廉把重庆的八省组织和汉口的行会联盟几乎等同起来,称为“早期的、非正式的自治组织”。当时我就觉得好惊讶:我们重庆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城市团体?以我对今天重庆的认知,似乎人们并没有什么“自治”气质。所以,我后来就特别留意关于这个组织的一切信息。然后发现,其实关注它的人还挺多的,我自己十年前发表的论文也是把它当做商业组织来看待的。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越到后来,人们越把八省客长作为商人,或者商人的联合组织来看待。但是后来我仔细地掰扯了从乾隆到光绪年间与八省客长相关的案件,我发现这些做了八省客长的人,他们很少自称是“商人”或者“商民”。比较早的时候,他们会说自己是“民”,咸同以后,他们越来越多地自称是“职员”——强调自己是给官府干活的。到了光绪年间,八省客长越来越多地是走行政程序遴选,而且还要拿官府的薪水,每年一百多两。所以福建会馆还为了谁能去当这个客长,吵了好多架,打了好长时间的官司。而且,八省的办公地点前后换了好几个,其中只有一个确定是商人捐钱修建的。连从商人那儿筹点儿钱修个办公室都那么费劲,你还敢说它是真的“商人组织”吗?如果按照邱澎生老师提出的商人组织操作性定义,那么,后两条“八省客长”显然是全都不符合的。
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是像罗威廉说的那样是“城市精英”(elite),尤其是在比较早的时期,好多案子里都说,这个人在他的原籍混得不好,或者是犯了事儿,就跑到重庆来,不知怎么就当上了八省客长。所以八省组织大概只能说是集合了相当数量的商人,以处理商业事务为一部分责任,而且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个组织,本身并没有排它性的“商人”或“城市精英”的角色设定,
最关键的是,它绝对不是自治组织。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处理很多事情,不管是商业的事情还是更广义的社会层面的事情其实都是有一条潜规则的,就是“官府优先”。没有官府的意志,它可以比较公允、比较有技巧地处理一些事情或者纠纷,但是也能看出来,它的威望不够,很多人也不听他们的。但是如果有官府希望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尤其是官府希望从这个诉讼或者这个事情中捞点钱,那他们是一定会去照办的。像这样一个既没有太多执行能力,又没有太多自主意志的组织,怎么可能是“自治组织”或“征服城市的组织”——它远远征服不了这个城市。光绪年间有一个八省客长向官府集体辞职的案例,你看了那个案卷之后,就能够深刻地感觉到八省客长彼时的无力和绝望。
从这个个案中我想说什么呢?
第一、如何理解“商人”。或许在传统时代的中国,商业的发展和经商者的成长,并不必然导致有这么一部分人,以“商人”为排他性的身份标签,拥有专属的属性、特殊的立场和组织。他们与传统社会的纠葛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深。你不能说商业的力量没有成长,但是它的成长可能是与既有的社会结构既共生又分化,既缠结又对抗的一种暧味状态。就像这些著名商人的肖像画,他们为什么要穿着官服来画自己的标准像?这是很有深意的。八省客长也是一样,他们或许与商业关系密切,但“商人”绝不可能是他们最认可的那个身份标签。
清代广东十三行商人
第二、自治、公共领域的问题。我至少不认为这个问题存在于清代重庆的八省组织,罗威廉的判断应该是有问题的。即使有“自治”或“公共领域”,可能也是越到后来,“自治”和“公共”的属性越弱。
行帮
行帮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
第一,就是行帮的自我管理能力。
行帮规程的制定过程,真的是一个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其实《大清律例》是不规定商业究竟要怎么做的,大多数的纠纷或问题出现了,你去查法条是没用的。但是大家就硬生生地磨出了一套既灵活又行之有效的规则。你想这样做,我想那样做,他想那样做,没关系,我们来协商,实在不行去打官司,打官司还不行,咱们就打一架,反正最后基本上都能求同存异,博弈出一个结果。还有,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有一个“上帝视角”,不管是个人决策还是集体决策,都会有错的时候,那也没有关系,我们不断试错、不断调整。制度和现实不符合了,那我们改就好了,实在不行就从头来过。
所以,制度就像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所以,这本书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有生命的制度史”。
第二,就是政府与行帮的关系。
政府与行帮的关系,和牙行、八省客长个案中看到的非常相似。一方面官府绝不一味地打压和剥削工商业者——事实上,官府相当重视他们。越是大的行帮,政府越会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和司法服务。因为这和地方政策、和地方的安定息息相关。你想,一个人数上千的行业组织闹事了,政府肯定是吃不消的,有可能地方官员的乌纱帽都要丢掉,他们承受不了这个后果。但是政府服务也不是免费的午餐,你得给政府提供各种报效,有可能是差务,有可能是帮着收厘金,还有可能是直接的捐款、报效。说白了,就是你要出钱去购买这种服务。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服务的质量可能不高,因为一个前现代化的政府,没有大数据,也没有各种部门的细致划分,也没有那么多的雇员。所以有的事情不是不给你解决,是真的解决不了。所以就有一些行帮觉得,我们又花了钱,你还办不了什么事,我还不如就不让你管了,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脚夫帮。他们后来和政府闹掰了,用暴力殴斗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说以前重庆人的性格很火爆,但至少从脚夫的个案可以看到,真的不是重庆人天生就这种性格,或者是因为吃辣椒太多,而是因为社会公共服务不够,许多社会规则不够清晰,所以大家只能诉诸这种最原始、最本能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大家总要想办法活下去呀,这或许就是一种被环境塑造起来的生存策略吧。我也不是说在当时重庆商业世界里没有“公共性”,而是说这是一种很稀缺的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或者说所谓“公共性”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维系着它的各种外部条件一旦发生改变,公共性的流失也非常快。
本次报告现场
最后对这项研究进行一个总结。
第一,就是清代重庆商业发展的阶段性。从我看到的材料来看,大致上乾隆至道光时期是它的生发期;咸丰中期到1891年重庆开埠,是它的成熟期;重庆开埠之后是它的困顿和衰歇期。1891年重庆开埠和清末新政是两个相当关键的节点。看起来这个市场越来越开放,政策也越来越励精图治、雄心勃勃,但是没成想全都帮了倒忙。
第二,是“以差(厘)驭商”的市场运行机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对牙行、八省客长、行帮的研究最后都发现了这个现象。这就说明,这是清代重庆市场最大的秘密之所在。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做法其实是《大清律例》明文规定不允许的,也就是说两百多年这个市场都是依赖一种违法的方式在运行!但是话又说回来,“以差(厘)驭商”并不见得完全是坏事,因为它至少把地方官府拉入了商业的游戏。否则,在行政经费不够、处理商业事务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地方官府是不会管商业的事情的。
但是这样一个游戏就需要谨慎地把握游戏规则。一方面,官府要学会自我约束,既要向工商业者伸手,但又不能超过他们的承受限度,而且市场的规模也要谨慎控制。市场规模太小,提供的利益驱动不够,很难把官府留在谈判桌上;市场规模太大,官府就会力不从心,乱了阵脚。
第三、官府是传统市场中“看得见的手”。至少从清代重庆的商业故事是可以看到,官府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是市场的控制者、汲取者,也是市场的合作者,最终也是由他们来承受市场失败的结果。所以至少在这个故事当中,官府才是更加抢眼的主角,是理解清代重庆市场更重要的一把钥匙。所以我猜想,在研究传统中国任何地区的市场时,哪怕材料中官府的角色不太清晰,但研究者也应该充分地考虑“国家的在场”。
第四、我们这一代人的经济史研究。
于我个人而言,从事经济史研究有两重思维底色:一是早年接受的传统中国“停滞落后”的印象;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传统经济社会再评价”。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在这项研究进行的过程之中,我常常会感知到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我看到的清代市场是相当有活力、蓬勃生长的。但是从一些微观的个案中,我又的确看到了诸多机制上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难道不是矛盾的吗?但直到最近两年,我才终于体会到,其实这两个方面整合起来可能就对了。如果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传统认识是“旧大陆”,对传统经济、社会的再评价是“新大陆”,那么把“新旧大陆”的资源整合起来,描绘一个各种因素和动力交互存在,既有成长又有阻滞的市场图景,难道不是更加符合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的自然状态吗?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这一代研究者与我们的老师辈相比,能带来一些知识增量的话,那或许就在于把“新旧大陆”的资源和洞见整合起来。
第五、这个研究还有很多未尽之处。比如对市场体量的量化评估、比如对金融业、盐业的深度描摹。所以希望这个研究能够成为一块铺路石,告诉更多的人,清代重庆这个“城市实验室”有着丰富的“实验数据”,也有着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需求和可能性。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