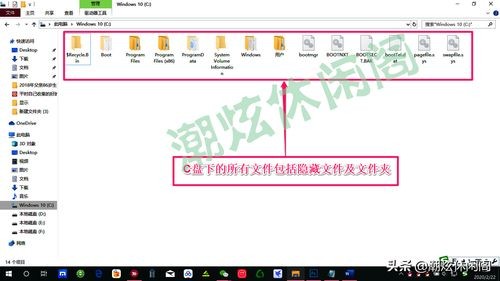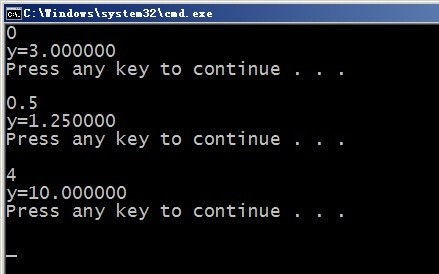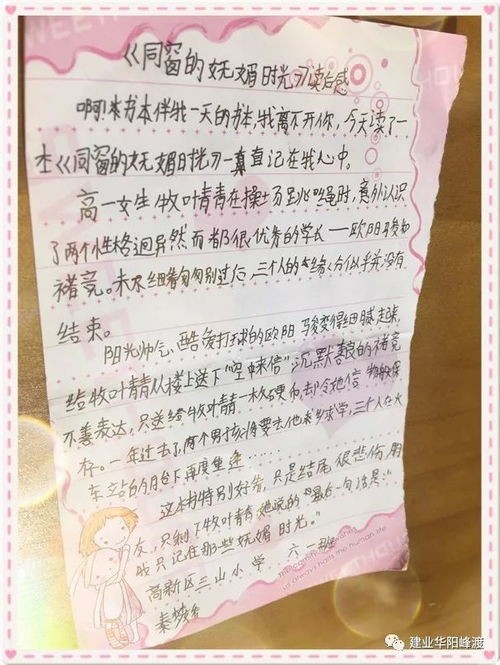唐吉诃德的故事。康赫 (视觉中国/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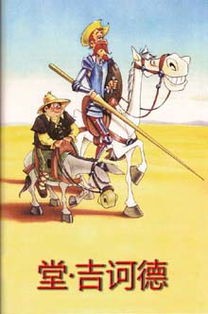
小说家、影像艺术家康赫创造的“独行客”郭嘏,从一开始就是伤脚的,这使得他的独行颇有滑稽意味:他不但是独行者,还是瘸行者。一只脚跳着前进,有时候比正常走路还快,但未免踉跄几步,痛快地摔个跟头/翻个筋斗。然后少年郭嘏那张帅气的脸挂满了泥浆,看不清哭笑。
这个姿势,不但是郭嘏的冒险姿势,其实也是以前的康赫的写作姿势。在近作《人类学》里被巨大的悲伤压制收敛了的,在第一个长篇《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收放自如的,在这部小长篇《独行客》里毫不掩饰,甚至刻意为之,有时邀人同欢,有时惹人反感。你会不解在这部作品中,平时从容调兵遣将的小说家康赫,为何完全丢掉了“克制”这一被当代小说家视为玉律的要求,把读者投到泥石流中。
不可以说郭嘏与康赫在借醉耍泼,虽然这些文字之任性、这个文本世界的放肆癫狂,比醉者的世界更横冲直撞、也更伤痕累累。艺高人胆大是康赫所恃,但更可能的是,《独行客》里16岁少年郭嘏,面对他那个高速崩坏的时代,眉头一皱,发出了与年龄不符的,70岁沧桑的怪叫,然后吐了一地。
像《启示录》以七个天使吹号展开毁灭的图卷,在不长的篇幅里,《独行客》穿插了多个重点人物与进城的郭嘏相遇,呈现多层交织的地狱于T城。包括杀手古里手与唐多多、走狗莫是莫非兄弟、歌手多夕与喇嘛旺堆、夺权者老项与他的情人泡泡……走马灯般此起彼伏,让这样一个小型地狱也奏出了长篇的多声部,他们的命运无始无终,混沌一片,只烘托出郭嘏对布比清晰的欲望与爱。
故事的开始像极了康赫最喜欢的电影大师戈达尔的一部冷门片子《周末》,从一辆进城的车子,渐渐汇入末世的洪流,遭遇各种灾难和人鬼莫辨的喜剧。故事结束也以一辆离开T城的长途汽车呼应,睡意绵绵的爱人终于彻底苏醒,不知将去向《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还是《人类学》里的另一个更宏大的喜剧。这是一个黑色的睡美人童话,郭嘏凭着一股少年心气和生于草莽的无产者乐观主义——他应该冠以这句鲍勃·迪伦的格言“一无所有的人无所畏惧,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与所有困难厮混在一起,然后突然把爱变成唐吉诃德的长矛,轻盈地把布比救出T城。
让这部小说彻底不同于其他在尘世中挣扎的现实主义者的,是他更接近于表现主义其黑暗阴冷的一面,奧托·迪克斯(Otto Dix)油画里那些活死人与纵欲者,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的穿行于癌病房与陈尸所的诗,与康赫的这个噩梦寓言是绝配。渐渐的,你分不清是独行客所经历的是老残游记还是聊斋志异,阴冷刻薄的前者与香艳诡秘的后者相混合,其漩涡一般的模样就是康赫意图呼唤的魔鬼。
郭嘏进城,应该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这些日常的狂乱与褴褛不堪延续至今吗?这是我阅读中常常想到的问题。狂乱曾经滋养了康赫乃至我这一代写作者的狂狷取向,也给予了我们的作品充足的能量,而近乎无产者的褴褛生活则是一种砥砺,没有被它啃噬掉尊严的人,就会像少年郭嘏那样百毒不侵。也许他从来不可能成为一个游侠,充其量是一个少年唐吉诃德,最后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枪不过是象征,真正的手枪是他自己与这种龌龊生活的格格不入。
假如我们依旧面对书里那些最龌龊的生活、不再褴褛赤贫但是更加龌龊……我们谈何超越?康赫的法子是让自己与郭嘏彻底自由,用奥登的诗《小说家》里的话就是“在龌龊堆里也龌龊个够”,让他们的自由更甚于T城那些苟活着的人的消极自由。郭嘏可以从头到尾吃各种东西(包括废品车上藏着的一根狗腿)、信任任何女孩、在任何地方提枪就上,康赫则放纵其吹牛皮的能耐大展身手,厚着脸皮介入每一个冲突,不介意能否抽身而出。因为奥登的诗还这样要求:
“而在他自己脆弱的一身中,他必须尽可能隐受人类所有的委屈。”
廖伟棠